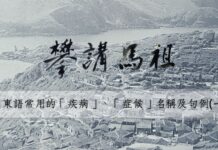繼去年之後,文化處於4月5日到9日,持續辦理福建籍配偶的走親之旅。陪著遠嫁馬祖的福建女兒回娘家走親戚。這些嫁來馬祖的姊姊妹妹,有的新婚才一、兩年,孩子猶在襁褓中;有的已在馬祖生活二、三十年,兒女皆已成人,甚至可以當依嬤了。
最近看到馬祖媒體報導,有關楊前縣長三體帆船即將下水的新聞,個人對此壯舉深感敬佩。楊前縣長對「亮島人遺址」的發現居功厥偉。此番帆船建造完成,是否有下一步計劃,我等鄉親多樂於聽聞。基於同村兼好友之誼,謹以本方言歌詞表示感佩與祝福之心意。
金、馬民防隊是反共抗俄、全民皆兵思維下的產物。戒嚴時代,前線男女除了公教及其眷屬,或女性首次懷孕三個月以上者,其他的都得參加。集訓期間,所有壯丁都須出席,影響收益自不在話下,其中以漁民不得出海作業「受傷」最重。時空背景相同,但各村發生的故事卻不一定相同,今天就以發生在牛角的往事和大家分享之。
當陳良福步出監獄大門,遠遠就看到姑丈林光興,蹲在水泥牆下抽菸,站在他旁邊的是莊建順大哥。監獄的水泥牆很高,十點鐘的太陽已經非常炎熱,圍牆上整排鐵絲網陰影,投射在馬路上,像是一叢叢怒生的芒花...
牛角是南竿的風口,南竿機場的北風尤其強烈。當時場上運動競技如火如荼的進行著,司令官也坐在司令台上觀賞。中將的將軍旗在他正對面的旗桿上飄揚著。突然一陣強風吹來,把代表他的將軍旗吹落到地面。說時遲那時快,一位憲兵立即衝上升旗台,拾起將軍旗,並且雙手持旗、挺胸立正、莊嚴肅穆的站在台上,文風不動一站就是三個多小時。
細珠和她的親戚都是中國境內少數民族「畲族人」,她們的母語是畲語,普通話(國語)是通用語。一踏進阿姨家,乍一看和一般漢族人的房舍格局差異不大,然而細看時,畲族特色一一呈現,首先是阿姨家準備的一桌子的畲族食物,有烏米飯、糍、月桃粽子、桂圓、糖果、蘋果、橘子等等,還有二三十杯加了少許白糖的熱開水,每一杯裡浮著二枚紅棗、擱著一隻匙子(喝完甜茶方便取食紅棗)。這完全是最高規格的接待,令人感動。阿姨說烏飯是每年農曆三月三日、月桃粽是端午節、糍是過年時必吃的節令食物。
「哪裡人?潭頭人,誰的孫?佬猴孫,誰的仔?鐲鐲仔。」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自從會說話開始,就被祖父母、父母親這麼教我們唸。長大之後有同學來家裡玩,總會被問到你是誰的孫?誰的仔?原來「哪裡人、誰家的子孫」在那時的馬祖代表的是一種社會網絡、身份的識別,如同早期馬祖人的小名常是「父子聯名、祖孫聯名」。
旅途倥傯,五天行程一下閃過。今天最後一站探訪曉澳鎮,李榮光(原名李仁光)、李嫻婷父女的家鄉。曉澳鎮位於閩江口北岸,與海峽東面的南竿津沙村遙遙相望,無怪乎津沙村許多人原鄉在曉澳。
幾天前看了金炎校長有關馬祖金雞母---中興酒廠的大作後,又勾起一些回憶。我不止一次在<馬資網>發表懷舊的文章,常提及自己是釀酒人家之後,今天有感而發,就借此機會,提供一些不為人知的軼事以為補白。
沰(馬祖話讀「ㄉㄚ˙」)有落下之意,所以海口人把漲潮說成「水漲」,退潮說成「水沰」。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「討沰」雖談不上什麼民生活計,卻是輔佐生活的重要作息。像一切古老技藝一樣,從工具到技巧,從語彙到禁忌,逐漸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工法與論述。
本次大陸走親「轉外家」,任務分工很細。蕭欽國經理及處裡同仁的後勤支援,將過程安排的從容有序。文佶伉儷等人,除了做影像紀錄以外,也是實際訪談者。因事先做足了功課,所以在提問時,都能切中要點。筆者兩次同行,旁觀、手記,內心感觸頗深。今以詩歌型態表達所見所聞,希望能為有意義的活動留下一些紀錄。
以下是高智煌先生的訪談,為求臨場真實,全文以第一人稱敘述。
依巴從小又黑又瘦,他是增財叔與秀娥嬸的第三個孩子。出生沒幾天,秀娥嬸便抱著紅通通的他,從下村跑到上村,再從東邊山跑到西邊山,四處央求還在哺乳的婦人,分一點奶水。因為秀娥嬸生下依巴前,三個月內連續夭折一對兒女,男孩5歲,女孩3歲。嬰兒出生的喜悅,絲毫沒有減少秀娥嬸的眼淚,她極度悲傷,再也無法擠壓出半滴餵養依巴的奶水...。
初次看到「海堡」二字,心中狐疑,是不是「海保」的筆誤?後來才知,這支於民國38年6月3日,於川石島成立的非正規部隊,約有4千多人,分散在岱山、四霜、浮膺、西洋、白犬、平潭、烏坵各島嶼。從北到南,有如海上城堡一般,扼守廣闊的福建海域。這4千多人的部隊,一度冠以「海堡」之名,其中約1千5百人駐守白肯;在糧餉不足、身分未明的情況下,有5年時間成為屏障台灣海峽一股重要的武裝力量。
九點抵福澳碼頭,劇組人員正辛苦地裝載布景道具,導演一家也來了。年輕演員看到岳母都非常興奮,他們中許多人初見劇中真實人物,紛紛合影留念。試圖在演出前的短暫時光,抓住當年蛛絲馬跡,填充各自表演內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