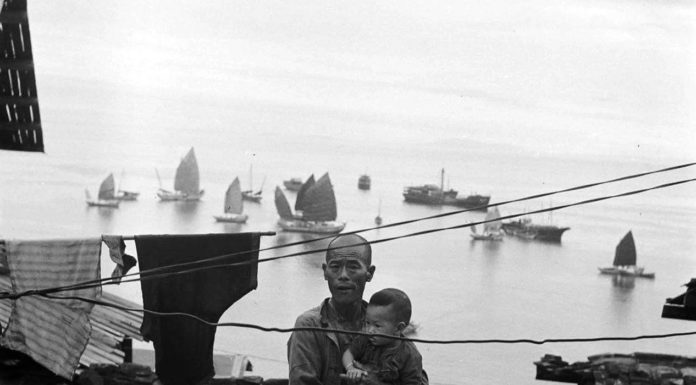幾天前看了金炎校長有關馬祖金雞母---中興酒廠的大作後,又勾起一些回憶。我不止一次在<馬資網>發表懷舊的文章,常提及自己是釀酒人家之後,今天有感而發,就借此機會,提供一些不為人知的軼事以為補白。
簡單的說,「躃火儽」就是「孩囝」賽跑,這是西莒特有的年節民俗活動。它選在元宵期間舉行,除了有祛災祈福之意義以外,又可達到競技聯誼、運動強身的效果。若能推廣,不僅讓馬祖「擺暝」文化更加多元,且對行銷西莒觀光當有正面意義。(文章中的字詞標音,請以羅馬字音標符號為準。)
馬祖話稱廚房為「灶前」,這是很傳神的說法。列島的傳統民居,最大的特色就是樓下少隔間,一進大門,所有「設備」一覽無遺,最顯眼的就是一座大土灶。今天,特選眼所能見的炊事家當為大家做介紹,並且說一些相關的雞毛蒜皮事。
把較大的魚開膛剖肚之後曬乾,馬祖話說「魚鯗」,也有鄉親稱「魚脼」,年輕世代的「後生囝」直接稱「魚乾」。這庶民食物不僅深受老鄉親喜愛,而且名稱牽涉到語言發展的有趣事情。今天就來說說與它有關的雜事吧。
「筅堂」也可以說「掃塵」、「掃年」…等。意思是年終大掃除,這是各地方都有的習俗。「筅」字只有一個讀音,但它的字義卻因詞性不同而有別。這個有意義的年節活動,卻因時代進步,生活環境的改善,使它的禮俗色彩淡化了許多。
馬祖話稱廚房為「灶前」,這是很傳神的說法。海島的傳統民居,除了茅屋以外,絕大部分是石牆、瓦頂、單層或兩層樓的小建築。這種建築最大的特色是樓下無隔間,一進大門,所有「設備」一覽無遺。今天,特選眼所能見的炊事家當為大家做介紹,並且說一說相關的雞毛蒜皮事。
「喜娘」馬祖話說「伴房嬤」,在傳統的婚禮上她是很重要的角色。新娘出嫁到婆家,內心難免不安,此時必須靠伴房嬤來安定情緒。她不僅是婚禮儀式的引導,能適時地炒熱氣氛以外,遇到想在口頭上佔便宜的賓客,還要會調解或排除。總之她是婚禮中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。
隨馬祖澳天宮進香團約二百人,一行人在2008年2月27日搭乘金龍號專船,上午由福澳港出發前進馬尾,轉往琯頭鎮再搭渡輪到壺江島,這座面積只有0.8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時候逼近一萬人,因漁場枯竭同樣面臨人口外移的現象目前常住人口數不到四千人,行政區劃分連江縣。這天縣政府官員和壺江的住民幾乎動員夾道歡迎,天后宮陣頭整頓後依序前往天妃廟會香,之後乩(芹壁、板里、白沙等)和天后鑾駕駐蹕宮內,人員各分配於民宅和學校。
看過桂香小姐對〈同物異名〉(七)的回應文之後,點點往事就湧上心頭。「揀蝦米」是漁村孩童難忘的記憶。我住牛角,此地曾是馬祖最大的漁村。每一年夏天各村落的民防隊訓練,上級派來的教育班長人數也最多。那時候,每天晚上民眾要輪流站衛兵,牛角人因人數多而久久輪一次,其他小村莊的人必須經常出勤務,有人說他們「一到天黑就哭」,這當然是開玩笑的話。
兩、三年前,前〈馬報〉記者林冰芳小姐來電詢問,有關〈大埔石刻〉碑文中 [犭隻] 與「獲」的問題。這件事引起我的興趣,遺憾的事是,該物件被玻璃罩圍著,無法摩娑原件一探究竟,只能如霧裡看花一般的略作分析。本文就是「推測」後的小小心得,謹供大家參考。
「馬拉松」是馬祖最近很夯的話題。對喜歡運動的我來說,真希望能藉舉辦大型活動的機會,進而「鼓動風潮」帶動地方的運動風氣,將運動和生活結為一體,成為日常習慣之一。
今天是立春,而且是春節之前的立春,這讓我想起一句老人家說的「年裡春,大寒接春,寒到你叩叩摏。」意思是說立春和大寒在同一年裡,例如今年(雞年)因為閏年,所以立春也在雞年裡,立春之前一個節氣是大寒(馬祖話唸ㄏㄢˋ,汗),立春在年前稱為「年裡春」,這樣的情況天氣特別冷,寒(馬祖話唸ㄍㄢˋ,幹)得你發抖牙齒打顫發出叩叩的聲音如同在摏臼一樣。
從有記憶開始,家裡廳堂長年擺置一座與人齊高的巨大木桶,外圍以竹條箍緊。依灼小時候經常踩著竹條攀上桶沿,俯視堆得像小山一樣的乾蝦皮。他也常常躲在屋角的漁網堆裡,跟妹妹玩捉迷藏。屋外橫躺幾根竹篙和碗口粗的篾繩,爸爸經常捧著碗公蹲坐上面吃點心。
馬祖話稱廚房為「灶前」,這是很傳神的說法。海島的傳統民居,除了茅屋以外,絕大部分是石牆、瓦頂、單層或兩層樓的小建築。這種建築最大的特色是樓下無隔間,一進大門,所有「設備」一覽無遺。今天,特選眼所能見的炊事家當為大家做介紹,並且說一說相關的雞毛蒜皮事。
依巴從小又黑又瘦,他是增財叔與秀娥嬸的第三個孩子。出生沒幾天,秀娥嬸便抱著紅通通的他,從下村跑到上村,再從東邊山跑到西邊山,四處央求還在哺乳的婦人,分一點奶水。因為秀娥嬸生下依巴前,三個月內連續夭折一對兒女,男孩5歲,女孩3歲。嬰兒出生的喜悅,絲毫沒有減少秀娥嬸的眼淚,她極度悲傷,再也無法擠壓出半滴餵養依巴的奶水...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![說〈大埔石刻〉中的「[犭隻]」與「獲」](https://voiceofmatsu.com/wp-content/uploads/voiceofmatsu.tw-2018-10-11_01-17-16_941035-1.懷古亭全景.jpg)